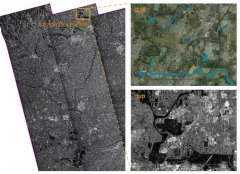|
【学科类别】刑事诉讼法 【出处】《刑事法评论》2015年01期 【写作时间】2015年 【中文关键字】法官;非法证据 【全文】 一、引言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分别以司法解释性文件和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法院解释》)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进一步予以细化。2013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以下简称《中政委规定》),在重申非法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同时,对讯问场所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问题也有严格要求。[1]2013年底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高法意见》)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进一步细化为“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同时在《中政委规定》的基础上,明确未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讯问以及讯问时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后果:排除相关供述。[2]至此,可以说我国已经确立了相对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那么,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效果如何呢?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效果,笔者曾经做过实证研究,发现调研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方面有若干成功经验,但也存在若干不足。[3]总体上来说,司法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很少。当然,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较少,而且在于很多法官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持消极态度。[4]据笔者调研,2010年7月至2014年6月,B市全市法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有114件,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案件有51件,申请启动率为44.7%;S市全市法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有51件,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案件有24件,申请启动率为47.1%;J省全省法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有451件,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案件有250件,申请启动率为55.4%。根据调研数据,全国其他地方的申请启动率也大致在50%左右。[5]考虑到很多申请由于没有提出明确的线索或材料,因而没有统计在内,实际上的申请启动率还会更低。对此,有学者认为,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难以激活的原因就是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6]笔者在数个省市调研时,很多律师抱怨法官不愿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即使启动调查程序也不排除非法证据。[7]很多法官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法官一般不排除非法证据,即使在很多时候其内心已经确信存在非法取证行为也不排除。事实上,根据学者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倾向于不排除非法证据。[8]那么,为什么司法实践中法官不排除或者几乎不排除非法证据呢? 经调研,笔者认为,法官之所以不排除非法证据,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法官不知道如何排除非法证据。对何为非法证据、证据合法性调查的程序等问题存在认知困难;其次,法官不愿排除非法证据。如有的法官认为在非法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排除非法证据会放纵犯罪;再次,法官不敢排除非法证据。如在排除非法证据有可能会导致全案判决无罪的情况下,有的法官就不敢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最后,法宫不能排除非法证据。如有的法官不仅知道怎么排除非法证据,也愿意且有胆量排除非法证据,但由于其不具有独立的裁判权而不能排除非法证据。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笔者所谓的法官不排除非法证据,并不意味着司法实践中没有法官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事实上,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已经收集了数十件全国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本文所谓的法官不排除非法证据,主要指的是一种倾向,即法官不排除非法证据的倾向。换句话说,除非迫不得已,法官一般情况下不排除非法证据。 二、法官不会排除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重要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其实质是由法院宣告检控方违反法律程序取得的证据丧失法律效力,是一种惩罚检控方程序违法的手段。[9]这种程序性制裁措施与传统的实体性制裁相比,在实体规则和程序运行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传统观点认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具体来说包括四种情形: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和收集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手段不合法。[10]依此观点,证据合法性包括取证主体合法、取证程序合法、证据形式合法和证据的内容合法四项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事实上,非法证据是根据英文“evidenceillegallyobtained”翻译过来的,其原意为“非法获取的证据”,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与此相对应,传统意义上的非法证据实质上指的是不合法的证据。因此,正如有学者所言,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应持狭义的理解,即仅限于以“非法定方法取得之证据”,主要考虑的是取证手段的合法性问题。[11]结合立法规定,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义上的“非法证据”范围非常有限,大多数所谓的非法证据的准确称谓应该是不合法证据。而不合法证据与(狭义的)非法证据在是否应当排除以及排除的程序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别,将两者相混淆就会带来司法实践中的困难。 然而,由于法官的工作量过重没有时间学习[12],部分法官基础较差不知道如何学习等原因,很多法官在短时间内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存在问题。如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很多法官经常问的同一个问题是何谓非法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戴长林庭长调研后也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和把握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仍存有争议,仍然经常混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13]有学者调研后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将“形式不合法”的证据当做“非法证据”予以处理的情形。[14]事实上,在很多时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弄清何谓非法证据,将一些“形式不合法”的证据误以为是非法证据而申请排除,而法官居然也将争议的“形式不合法”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调查。如有学者调研发现,在司法实践中,辩护词、判决书往往将此类因不符合“证据审查认定要求”的证据材料也视为“非法证据”。[15]由于对非法证据的理解存在问题,有些人将不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等同,进而产生不合法证据是否也需要排除的疑问。换句话说,司法实务人员普遍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同样是违反法律获取的证据,为什么有的需要认定为非法证据进而予以排除,而有些则不需要排除。关于这个问题,恰如林钰雄教授有言,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下,取证规范不计其数,各自的规范目的有别,取证违法的形态轻重更是千奇百怪,不一而足,难用一个简简单单的“违法=排除”公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16]另外,很多法官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在非法证据的真实性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是否还要排除非法证据?最终的结果是,在更多的时候,由于法官对非法证据的理解存在不足,不会排除,而干脆不排除。 当然,法官对何谓非法证据以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的理解存在诸多不足,除了个人原因外,还与立法的模糊有关。以非法供述为例,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然而,第54条却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何谓“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2012年《法院解释》第95条第1款规定,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显然,我国立法采取的是“宽禁止、严排除”的模式。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作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很自然的一个疑问是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获取的供述是否应当排除?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如龙宗智教授认为,采取威胁的方法,如使嫌疑人精神上剧烈痛苦,被迫做出供述的,应当予以排除;司法解释实际上排除了引诱、欺骗方法获取的证据被作为非法证据酌定排除(区别于刑讯逼供的法定排除)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司法解释有悖于刑事诉讼法严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规范精神。但由于司法解释已作出如此规定,非法采用引诱、欺骗方法获取口供难以援引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只能采取其他方式处理。[17]有学者则认为,一旦威胁引诱欺骗手段的使用带来了精神上的剧烈痛苦,则应当视为排除的对象。使用亲情、家庭关系进行威胁、引诱与欺骗的做法,已经触动了人类良知的底线,超出了公众伦理道德的可接纳边界,应当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坚守人类良知的底线,捍卫亲情伦理关系这一社会存在的基本运转条件。[18]还有学者认为,如果威胁、引诱、欺骗的行为严重违法或者严重违反道德,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由此获得的供述应予以排除,对于这样的威胁、引诱、欺骗行为可以纳入到“刑讯逼供等”的“等”字范畴之中[19]根据后两位学者的观点,通过引诱、欺骗方法获取的供述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应当予以排除,但排除的标准又有所不同。由此可见,在立法上规定模糊,而理论上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通过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供述是否应当排除、如何排除,法官确实存在一定的困惑。 司法实践中,另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是重复供述是否应当排除以及如何排除。反复多次讯问以固定口供,并掌握供述变情况,是侦查讯问的基本要求。但如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迫使犯罪嫌疑人供述,势必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严重心理影响,以至于此后讯问即使不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犯罪嫌疑人仍会在前述心理影响下继续供述。然而,由于立法没有明确规定重复供述是否应当予以排除,理论上对此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20],导致实践中对于是否应当重复供述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此外,即使认为重复供述应当排除,但对如何排除也有不同认识。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应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与重复供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标准进行区别对待[21],即非法取证行为的持续影响效力理论;少数学者则主张全部排除[22],主要理由是区别对待说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此外,律师的观点一般也是全部排除[23],很多律师在法庭上也是如此主张的。笔者调研发现,司法实践中,既有排除重复供述的案例,如J省、C市(2014年6月以后)有多个排除全部重复供述的案件,也有重复供述一律不排除的案例,主要的理由是排除重复供述没有法律依据。如G省的一份判决书中显示,法官认为辩方要求排除重复供述的辩护观点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但总体上来说,很多法官倾向于不排除重复供述。如C市法院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期间排除非法证据的24例案件,全部排除的是非法供述,但没有1件排除重复供述,最终大部分案件依据重复供述定罪。 除了上述实体问题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也存有若干争议。如何时进行证据合法性调查、何时作出证据合法性裁判。事实上,关于上述两个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已有明确规定。[24]根据这一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先行调查”原则和证据能力优先于证明力原则,即原则上应当对证据合法性问题先行调查,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在作出是否排除争议证据的决定后再对争议证据进行宣读、质证。考虑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参与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还明确指出,决定既可以当庭作出,也可以休庭后经过慎重研究再行作出。[25]然而,或许是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或许是总结贵州“小河案”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之争引发“辩审冲突”的经验教训[26],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上述问题没有规定[27],2012年《法院解释》仅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时间作了灵活规定,即第100条第2款规定: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在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后进行,也可以在法庭调查结束前一并进行。而对于在证据合法性问题解决前是否允许对争议证据进行宣读、质证的问题则没有明确规定。对此问题,陈瑞华教授认为,“在被告方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情况下,法院即使不中断法庭调查程序,也必须将有争议的公诉方证据排除于法庭调查之外。法院这时只能对无争议的控方证据启动法庭调查程序;在法庭调查结束之后,再对被告方申请排除的控方证据启动程序性裁判程序”。换句话说,“即使在不适用先行调查原则的情形下,法院也要遵循证据能力优先于证明力的原则”。[28]最高人民法院戴长林庭长亦认为,要注意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结束前不能对证据宣读、质证。[29]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是定案根据而不是证据资格,因此,我国审判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可借鉴德国的做法,在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裁判时一并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作出裁断。这也符合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及实际情况。[30]有法官持类似观点。[31]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庭往往对证据合法性问题进行调查后,并不立即给出排除与否的结论,而是对争议证据进行传统的法庭调查活动,然后在裁判文书中将排除与否的结论与实体性裁判一并作出,在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有些法官甚至在裁判文书中对于是否排除非法证据也没有明确的回应。 客观地说,立法模糊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法官能够恰当解释法律,根据立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将相关规定解释成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完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由于立法模糊所带来的问题。然而,一方面由于部分法官的理论素养存在不足而无法在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恰当地解释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法官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法官没有权力也不敢贸然解释法律。上述两方面的原因结合,造成我国的法官僵化有余而能动性不足。有学者认为,在难办案件中,法官无论怎样决定都必须并首先作出一连串政治性判断。[32]事实上,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法官是无法进行“一连串政治性判断”的。据笔者调研,我国法官的法解释能力存在不足,部分法官对法律条文的内涵以及各条文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在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往往更是不知所措。在法院绩效考评的背景下,只要遇到稍微复杂一些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法官都会选择请示领导,在领导也拿不准的情况下,往往又会请示上级法院。然而,由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属于“审判之中的审判”,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频频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情况下,法官难以在每一起案件还未审理完毕之时便频频请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法官便会想方设法回避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或者置之不理,或者与案件实体问题在裁判文书中一并处理。 三、法官不愿排除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是在具体个案中由法官具体操作的,因此,法官能否坚守中立地位公正司法至关重要。[33]根据我们对法治的一般理解,法官角色应该是中立时[34],不应该偏袒、维护一方而打压另一方。然而,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并没有恪守中立地位,而是愿意充当第二公诉人。有律师认为,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官能够维护客观中立的法官理想形象,但也有不少法官则是另外一副模样[35]: 在讯问被告人阶段,无论公诉人在正常的发问之外对被告人施加压力、进行胁迫,还是与被告人进行争辩,法官都无动于衷,而当辩护人的询问不符合其心理预期时,则毫不犹豫地予以打断;在举证质证阶段,无论公诉人的举证如何冗长,法官都毫无异议,而当辩护人就证据中有利于被告人的部分展开说明时,法官会毫不掩饰地表露其内心的不快,并毫不客气地予以警告、制止;进入法庭辩论环节后,法官可以任由公诉人充分全面地发表公诉意见、进行大段的法制教育,而当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时,要么以辩护意见与法庭调查的发言有重复,要么以辩护人的最后陈词与案件无关为由,极不耐烦地打断。这样的法官,俨然是一副官老爷训斥刁民的态度对待辩护人,把自己当作对犯罪进行追诉的“第二公诉人”,我们可将其模型化为“追诉型法官”。 根据笔者长期对司法实践的观察,上述说法并非夸张,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追诉型法官”。毫无疑问,从理论上来说,法官的角色应当是一个中立消极的裁判者。然而,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的刑事庭审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庭审存在巨大的差异,它更为关注的是被告人在庭审中的“态度”,是一种“教化型庭审”。刑事庭审的教化一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即表态、展示、教育与悔过“四部曲”。[36]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明显不同的是,我国的司法不仅要负责案件的裁判,还负有一定的社会治理功能。[37]由于法院和法官长期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使得部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能不自觉地有一种追诉的意识。此外,还有部分法官认为,传统的案件事实审理才是庭审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上述诸种因素的结合,使得部分法官具有一定的追诉意识,一般不愿意排除非法证据,特别是在法官认为排除非法证据将会放纵犯罪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种情形正如有学者所言[38]: 在过度强调案件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法庭不仅没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动力,而且往往形成结果中心主义或者以实体结果否定诉讼程序的思维方式。进一步而言,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只要法庭认为犯罪事实能够得到证实,即使辩护方能够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控方存在非法取证行为,法庭也不会认定和排除控方的非法证据。 当然,随着法治理念的深入,在重提“庭审中心主义”的大背景下[39],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情况下,法官的独立公正司法理念将会进一步提升,这种愿意充当“第二公诉人”的“追诉型法官”会越来越少,有些法官也会认识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必须有所取舍,即使存在放纵犯罪的风险,也要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然而,即便如此,仍然会有很多法官不愿排除非法证据。 除了甘当“第二公诉人”或者基于惩罚犯罪的需要而不愿排除非法证据外,还有一些法官则是因为熟人社会的“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而不愿排除非法证据。有学者认为,熟人社会存在一种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它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熟人之间的“情面原则”;二是情面原则衍生的“不走极端原则”;三是情面原则衍生的对待陌生人的“歧视原则”;四是情面原则衍生的“乡情原则”。[40]换句话说,熟人社会注重内外之分,对外部人不讲情面,对内部人则不讲原则。事实上,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小型的熟人圈子,很多法官和检察官或许还是同学,一些检察院的领导曾经是法官,或者一些法院的领导曾经是检察官。在这样一个小型的熟人圈子里,相互之间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之间可能会构成一个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存在的有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在这里也会存在,而且越是在侦查技术落后因而更有可能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偏远地区,这种乡土逻辑的影响越是强烈。由于乡土逻辑的“情面原则”和“不走极端原则”,法官一般不愿意排除非法证据,更不会认定存在非法取证行为。传统的做法是,法官发现案件证据存在问题,往往会要求公安机关作出说明,或者进行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往往以“不能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为由排除非法证据,然后以审前重复性供述定罪。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发生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判决无罪的情形。 四、法官不敢排除非法证据 随着刑事法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大部分法官知道如何排除非法证据,也愿意排除非法证据,但一系列现实原因逼迫其不敢排除非法证据。在现代刑事审判制度中,“为确保法官保持公正无偏的地位,现代各国法律一般均建立了保证法官独立自主地进行审判的机制,使法官在审理和裁判时不受外界的不当干预、控制和影响”。[41]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就确保法官中立裁判的机制而言,我国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定罪量刑时会面临来自审前机关的巨大压力[42],在排除非法证据时亦是如此。[43]陈光中教授所举的一个案例非常具有典型性[44]: 以王某为首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该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一审过程中曾多次提出在侦查阶段遭到刑讯逼供,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予理会。一审作出有罪判决后,被告人王某等人提出上诉,认为本案在侦查阶段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和公安人员违背事实编写笔录的问题,对王某定罪所依据的主要证据都是同案被告人和王某本人在刑讯逼供下所作的不实供述。二审期间,辩护人提出的证据主要有:①王某等人亲笔书写的刑讯逼供材料,里面描述了非常具体的非法取证时间、地点、人员、方式以及逼供的内容等信息。②侦查人员李某的亲笔证言,证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侦查人员在办案时对王某等人进行残酷刑讯逼供,编写不实讯问笔录,威逼诱骗其他被告人把责任往王某身上推,并将许多犯罪嫌疑人没有讲的话都写到了笔录上面。③在看守所和王某关在一个房间的证人证明王某被提外审14天后才送回,腿、脚肿大近三倍,回来站不稳要靠人扶。在提出以上证据后,省高院曾准备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但囿于外部压力,最终没有启动合法性调查程序,二审维持原判。 根据陈光中教授的介绍,该案确实应当排除非法证据,但由于“外部压力”而最终没有排除,甚至根本就没有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那么,所谓的“外部压力”是指何种压力呢?笔者调研发现,所谓的“外部压力”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审前机关的压力;二是被害方的压力;三是社会舆论的压力。在被害人一方反应强烈,社会舆论较大的情况下,一些党政部门也会向法院施加压力。在案件有可能因为排除非法证据而判决无罪的时候,这种压力最为明显。有学者认为,程序性制裁的关键环节是法院必须要“勇敢地”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判决无罪。[45]然而,现实中很少有法院会“勇敢地”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判决无罪,在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当然,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法院排除非法证据可能不会遇到上述所有压力,司法实践中,最经常遇到的压力是审前机关的压力。恰如有学者所言,“由于法官们对侦查办案机关多是持同情态度的,而认定刑讯逼供又会影响到办案单位及个人的重要利益,进而使自己身上背负的压力增大,因此难免会更加谨慎。一旦因排除证据而不能顺利定案,就容易导致公检法等政法机关之间的失和,给法院今后的工作带来负面影响”[46]面对审前机关的压力,一些法官就会选择不排除非法证据。 事实上,在有些地区,即使排除非法证据只影响部分案件事实的认定,最终不影响定罪而只影响量刑,但法官面临的压力仍然很大。笔者在东部数个经济发达省市调研时,参与座谈的法官一再强调排除非法证据面临巨大压力,即使排除非法证据不影响定罪,公安和检察机关也会有相当大的反应。如被称为“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的浙江宁波章国锡案,一审法院以检察机关举证不力为由排除了被告人的审前有罪供述。在此基础上,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章国锡受贿7.6万元仅认定0.6万元,且认定其自首,最终对章国锡定罪但免予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抗诉。在二审过程中,公诉机关提请行贿人周某、史某出庭作证,提交了行贿人史某的同步审讯录像、章国锡同步审讯录像以及侦查人员关于讯问过程合法性的证言。在此基础上,二审法院认定章国锡受贿7.6万元,判处有期徒刑2年。[47]根据有学者的研究,公诉人最关心的问题是被告人能否被定罪,其次关心的问题是法院判决是否改变指控的罪名,最后才是对于指控的事实能否全部认定。[48]因此,章国锡案一审法院认定章国锡受贿0.6万元,已经给了检察机关的“面子”,但检察机关仍然提起抗诉,最终,二审法院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对一审判决改判。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获悉,章国锡案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立即对一审法院执行局的某位执行法官展开侦查,最终逮捕该执行法官。调研中,很多法官反复强调,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一个重要的威慑力量,即使某办案法官自身廉洁公正,但也不敢或者无法毅然排除非法证据或者判决无罪,因为法院领导担心排除非法证据或者判决无罪引来检察机关的“报复”。 在职务犯罪中,情形更为复杂。有学者认为,在职务犯罪中还要面对纪委有关调查材料的权威性和难以质疑性,致使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也就尤显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该学者的调研问卷显示,66.6%的刑事法官认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障碍来自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障碍和法院、法官司法权的相对弱化[49]司法实践中,经常有被告人辩称在纪委阶段遭到刑讯逼供,在侦查阶段的重复性供述是受之前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而作出的。辩护人往往认为,这种情形下获取的审前重复性供述均应当予以排除。对此,有学者认为,应当排除这种类型的重复供述。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射程”并不局限于侦查程序,只要违法取证行为与证据之间有因果关系,即使是在侦查前程序中进行的违法取证,也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射程”之内。[50]但法院一般认为,纪委是否存在非法取证情形不属于法院评价的对象,进而对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理睬。事实上,最近已有法院在公开权威刑事审判刊物上明确表示,对纪委调查情况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不予评价,即浙江湖州法院审理的褚明剑受贿案。该案二审法院的观点颇具代表性[51]: 我国的刑事诉讼,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的程序,查明案件事实,应用刑法确定被追诉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受到刑事处罚所进行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的活动。因此,纪委调查不属于刑事诉讼活动,纪委调查取得的材料不作为证据使用,纪委调查情况也不属于刑事审判内容。 该案例分析发表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办的权威刊物《刑事审判参考》上,作为指导案例供全国各级法院参照。虽然《刑事审判参考》上发布的指导案例与最高人民法院分批次分布的“指导性案例”在效力上有所区别,但在下级法院法官的心目中,《刑事审判参考》上发布的案例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除非有充足的理由,一般都会在司法实践中参照刊物上刊登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是绝对不敢排除与纪委有关的重复供述的。 五、法官不能排除非法证据 任何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都需要时间,法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了解亦不例外。伴随着法院系统的培训和法官实践经验的总结,法官不会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会逐渐减少乃至最终消除;伴随着法治理念的深入以及对自身定位的重新评估,法官不愿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也会逐渐减少;伴随着对依法治国理念的宣扬和审判独立的强调,部分法官也会勇敢地排除非法证据,甚至最终勇敢地判决无罪。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法官即使有心排除非法证据,但由于某些原因,最终仍然不能排除非法证据。具体来说,主要是指两种情形,一是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表面上相互印证,法官即使内心确信存在非法取证行为也不能排除非法证据;二是由于法院领导不同意,法官不能排除非法证据。 当法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后,大部分公诉人都会向法庭提交若干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如情况说明、入所体检表、部分录音录像等,在上述证据材料仍不能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情况下,有些公诉人还会提请法庭通知与被告人同监室的人员、看守所体检医生、看守所工作人员等出庭作证,甚至还会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此时,公诉方的举证在表面上形成了一个相互印证的证据体系。换句话说,这些证据从形式上看能够相互印证,控方似乎完成了举证责任。所谓印证证明,就是要求认定案件事实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证据,其证明内容相互支持(具有同一指向)排除了自身矛盾以及彼此间矛盾,由此而形成一个稳定可靠的证明结构。[52]然而,在不能保证情况说明、入所体检表等证据材料真实性的情况下,这里的印证可能仅仅是形式上的。[53]所谓自由心证,是指法官在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的指引下,除遵循个别证明力规则外,对于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和全案证据的证明力自由判断。反观我国,“印证证明模式”中虽然也允许法官自由判断证据的证明力,但这种模式中更多强调的是“印证”,由此导致我国的法官更多地考虑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而不注重通过交叉询问等方式保证证据的真实性。由此可能会导致这种倾向:一些案件法官内心对于相互印证的证据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对全案证据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没有产生内心确信,但由于证据材料在形式上达到了相互印证的要求,不得不判决有罪。换句话说,由于对印证证明要求的机械理解,司法实践中存在虚假印证和片面印证的情形,其中,所谓虚假印证是指以不可靠的证据材料作为印证证明的中心进而得出虚假的印证关系[54],而所谓片面印证,又可以称为选择性印证,即对于在案的证据材料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从而在表面上形成一个相互印证的证据体系,而对于被告方的辩解或者质疑则视而不见。 事实上,在一些案件中,法官对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内心并没有排除合理怀疑。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法官如果内心仍存在合理怀疑,当然不能认定取证程序合法。但在检察机关坚持认为证据系合法取得的情况下,法官往往会面临形式证明与自由心证的矛盾问题。试举一例[55]: 某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被告人提出侦查人员向自己身上泼凉水,然后用风扇吹干,因为当时正值冬季,被告人表示自己实在无法承受就作了有罪供述。法官到看守所实地调查时发现看守所办公室里确有一台电风扇,而且没有储藏起来,由此怀疑最近被人使用过。但是在后来的庭审中,公诉方举出看守所工作人员证言,证明该电扇没有被任何人带出办公室,再加上公安机关出具的没有刑讯逼供的情况说明,遂认定侦查人员系合法取证。 在类似的情形下,法官基本上无法查清是否有非法取证行为,但又不敢贸然认定有非法取证行为,一般也不会贸然排除非法证据。事实上,根据笔者的调研,司法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要么是因为体检记录上显示有伤、有证人证实有伤或者同步录音录像显示有不规范甚至明显违法的审讯行为,要么是因为应当录音录像没有录音录像、应当送看守所羁押而没有在看守所且无法排除非法取证的合理怀疑。否则,仅仅因为法官内心确信或者怀疑有非法取证行为,是不可能排除非法证据的。 根据法院内部的规定,在排除非法证据而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情况下,承办法官需要将案件提交院庭长讨论,最终由于院庭长不同意,承办法官不能排除非法证据。当然,承办法官也可以不将案件提交讨论而直接排除非法证据,但由于裁判文书需要院庭长审签,如果院庭长不同意承办法官最终仍不能排除非法证据。 那么,法院领导为何不同意排除非法证据呢?据笔者观察,这与法院领导面临的巨大压力有关。首先,是审前机关的压力。在公检法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一体化司法体制下,法院在很多方面需要公安检察机关的配合。比如,法院办理的案件需要公安机关及时补正,如果没有补正就作出判决,在新的证据出现后,由于我国既缺乏程序安定的理念[56],又没有禁止双重危险的制度设讯[57],在有罪必纠理念的指导下[58],所作出的判决可能会随时被改判。在加强审判管理,注重绩效评估的制度背景下[59],改判很可能就意味着法院在绩效评估中拿不到好的成绩,进而可能影响法院院长的仕途。再如,检察机关拥有的抗诉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对法院也是不小的威慑。由于我国法院“对各级领导干部普遍适用‘一岗双责’的双重责任制度”[60],法院领导即使自身没有问题,也无法保证全院所有干警均廉洁守法。只要出现一例法院干警贪腐现象,一个法院一年的工作等于白干,不仅会丧失各种评先评优的机会,甚至还会影响到普通法官的物质利益。此外,法院领导还要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其次,是被害方与社会舆论的压力。正如有学者所言,“现实中,被害人如对判决不满意,往往采用上访、示威甚至抬尸游行等举动给法院施加压力”。[61]而在“涉诉信访已经成为法院工作非常重要的内容”的情况下,地方各级法院更是直接处在访民和上级党委政府的双重压力之下,以至于信访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法院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62]法院在排除非法证据时,不可能不考虑排除非法证据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被害方反应。在排除非法证据可能判决无罪时,更是如此。[63]此外,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一些法院不愿意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将自己卷入舆论的无休止的争论中。最后,是党和政府惩罚犯罪的要求所带来的压力。一般来说,命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职务犯罪案件相较其他案件更有可能存在非法取证行为,而这些案件恰恰也是党和政府较为关注的案件,这些案件要么被害方反应强烈,要么在当地有较大影响,要么涉及党的反腐斗争,一旦这些案件涉及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可能需要政法委协调案件。事实上,随着佘祥林、赵作海等一系列冤错案件的曝光,政法委协调案件的做法和弊端已经引起人们的反思。[64]但可以肯定地说,政法委协调案件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根据上文的分析,法院领导不会允许法官“随意”排除非法证据,更不会允许法官因排除非法证据而判决无罪。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法院领导不排除非法证据是如何可能的呢?司法行政化,即以行政性的方式审判案件并管理法院和法官,是我国司法运行与司法建设长期存在而未能解决的问题。[65]正是在司法行政化的制度背景下,“为了避免违反强制性规范而受到惩罚,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为了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66],法官很难不听从法院领导的指示。具体来说,法院内部通过行政管理以及各种资源的再分配来实现对法官个人行为的控制。这种情况正如有学者所言,“这个群体和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群体有足够的力量来惩罚叛离者或奖励依从者,而在一定限度内,奖赏越多,威胁越大或正当理由越多,依从性就越大,而且一定的群体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环境氛围,这种情境的压力会使得一个人即使在没有受到明显的奖赏或威胁的情况下,也会按照群体的意见去做”。[67]具体到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如果法官不听从法院领导的指示,很可能会被贴上“不听话”的标签,很可能会被调离审判部门,从此被打入“冷宫”。 具体来说,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院庭长审批案件机制以及审委会讨论案件机制,为法院领导控制法官的司法裁判行为提供了具体的制度支撑。 就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来说,以是否有明确的内部要求为标准,可以将司法实践中的院庭长讨论案件分为两类,即法院内部有明确要求的“法定讨论型”,以及法院内部没有要求,承办法官觉得“不踏实”等原因主动要求讨论的“裁量讨论型”。讨论的内容包括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案外因素对案件处理的影响。具体流程如下:案件分到承办法官处,承办法官经过庭前阅卷、开庭以及庭后阅卷,如果发现承办的案件属于上述几类,将向庭长汇报,由庭长负责联系分管副院长,然后确定讨论案件的时间。讨论案件一般在分管副院长办公室进行,首先由承办法官将查明的案件事实以及现有的证据归纳一下,然后说明本案中需要讨论的问题。分管副院长对一些不清楚的情节或认为比较重要的方面会进一步地追问承办法官,待承办法官将案件事实叙述清楚后,分管副院长会问庭长的看法,然后再给出自己的观点。[68]一般来说,讨论案件时最终会以院长的意见为准。如果院长基于各种考虑,决定不排除非法证据,法官几乎不会违抗领导的指示。 当然,并不是每个案件都需要院庭长进行讨论,且有些法官基于各种考虑也可能最终没有将案件提交讨论。此时,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院庭长审批案件机制起了重要的作用。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是指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院长、庭长对合议庭评议案件的结论或意见进行审查、核定和监督。[69]院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却一直遵循这一惯例。在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法院内部审判组织及其权限作出具体规定后,实务界对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有法官认为应该废除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70],有法官则认为应该坚持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71],还有法官持折中意见。[72]第一篇讨论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的文章还发表在《人民司法》上[73],结果,该文作者的同事,北京二中院法官孙常立也在《人民司法》上发文,认为院庭长审批案件既是法律所允许的,也是实际工作所需要的,应当继续执行。[74]最终,《人民司法》1981年第6期发表社论,从历史、法律和现实三个角度论述院庭长审批案件不应该取消,但需要进一步予以完善。[75]此外,在同一杂志上,还刊登了著名法学教授徐益初的关于院庭长审批案件和司法独立的文章[76],并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审批案件的办法(试行)》,共有6个条文,对院长和庭长的审批范围和权限作了规范。紧随其后,各地法院纷纷制定有关案件审批制度的内部规章制度。[77]此后,仍不时有法官撰文呼吁改革或者废除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如有高级法院院长撰文呼吁改革院庭长案件审批制度,逐步下放案件审批权限。[78]还有法官认为,案件审批制度是传统审判管理的核心制度。案件审批制度存在诸多法理缺陷和实践弊端,应该废除院庭长的案件审批权限,但赋予院长、庭长提请复议权,发挥其管理和监督作用。[79]有些法院甚至还尝试将案件的“审批权力下放”,据有法官介绍,深圳中院在1994年就已经将部分案件的“审批权力下放”。[80]就规范性文件而言,《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第18条明确规定: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依审判职责签发裁判文书。201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第7条则规定,特定类型的案件可以由审判长提请院长或者庭长决定组织相关审判人员共同讨论,合议庭成员应当参加。但是,上述案件的讨论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不影响合议庭依法作出裁判。综上,尽管有理论上的反对,规范性文件也提出要“充分发挥合议庭的职能作用”,但司法实践中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仍然照常运行。 上述情形,正如有学者所言,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层级汇报研究和签发制度,看似是上位法官对办案法官意见的审查和批准,实则是一种案件审批行为,这和无处不在的行政审批没有本质区别,并由此产生了审判中的行政化现象。[81]然而,审判权力运行的行政化也无法保证所有的法官都会听从领导的指示,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听话”“有个性”的法官。此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作为一种合法手段,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个别情况下,承办法官也会坚持原则,不同意院庭长的意见,此时,院长往往会提请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相关问题。根据201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第11条第2款的规定,合议庭没有建议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院长、主管副院长或者庭长认为有必要的,得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众所周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结果,合议庭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承办法官想排除非法证据,但法院领导基于各种考虑决定不排除非法证据,承办法官最终是不能排除非法证据的。 六、法官为何能不排除非法证据 由于两个原因的存在,法官不排除非法证据并非易事。一是非法证据是否应当排除法律有明确要求,法官不排除非法证据可能会面临合法化危机;二是审级制度的存在,一审判决还要面临二审法院的审查,法官不排除非法证据可能面临二审改判的风险。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1.证明标准的模糊性或弹性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机会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7条第1款、第8条以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法官对证据收集合法性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应当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1条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1款的规定,检察机关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1条、第12条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82]表明看来,上述规定已经相当清楚,法官只要依照规定办理即可。然而,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诉讼认识是一种特殊的认识,事实认定者通过证据材料认定案件事实,这种认识本质上属于事实认定者根据证据材料判断作为证明对象的命题与客观案件事实是否符合,表现为事实认定者的心证程度,即内心的确信程度。[83]因此,作为心证的产物,诉讼认定事实的标准除从主观上提出要求,别无他法。[84]所谓的证明标准,事实上就是对法官内心确信程度的要求,具体可表述为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当然,这种主观上的内心确信度并非毫无客观根据,如需要接受证据裁判原则的限制、经受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的检验,并且这种心证结果还要具有可重复性,即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面对相同的证据材料时一般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体现为合议制度和上诉审查制度等。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言,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并不是一个没有任何弹性的标准。[85]另外,“一些英国法官和学者认为,证明标准应该是弹性的或浮动的甚至是滑动的,即应根据系争对象的不同区别对待”。例如,丹宁勋爵在BatervBater案中指出:“在刑事案件中,指控必须得到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但在这个标准之内可能也有不同的证明程度。”而在美国,“某些学者和法官持有同样的观点”[86],如达马斯卡教授认为,对外在事实和精神事实的把握,人们实际上都是区别对待的。例如,关于被告人是否向死者开枪的问题,在实践中会设立非常严格的证据要求。在确定是否存在伤害或杀人意图时,证明要求就会宽松得多。[87]由于证明标准所具有的这种弹性,对于辩方举示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是否使得法官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以及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是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答案,需要法官结合案情与在案证据慎重判断。换句话说,法官在决定是否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以及是否排除争议证据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有自由裁量权,就有被滥用的可能。实践表明,法官确实利用证明标准的模糊性而随意拒绝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在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后又随意拒绝排除非法证据。 2.案件请示制度消解了审级制度的功能 根据规定,下级法院要接受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88]那么,上级法院如何指导下级法院呢?实践中存在的案件请示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方式。所谓案件请示制度,是指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处理或程序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予以答复的制度。[89]在我国,立法上对于案件请示制度并无明文规定,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由来已久,并已固化为法院的一种办案方式和审判惯例。[90]对此,有法官认为,案件请示制度的存在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共产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是案件请示制度形成的历史渊源;(2)最高人民法院于1986年3月24日和1990年8月16日下发了《关于报送请示案件应注意的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报送请示案件应注意的问题补充通知》,对案件请示加以规范,使之制度化。(3)随着目标管理责任制、错案追究责任制的推广落实,下级法院一审案件的改判、发回重审的比率是衡量其办案质量的重要参数。对下级法院及审判人员而言,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能否被维持,意义重大。因此下级法院对较疑难的案件,为稳妥起见,积极报送请示。该法官还认为,案件请示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存在9个方面的问题。[91]还有法官认为,为避免案件在二审被改判或发回重审,或者是为了应对各种压力将矛盾上交,司法实践中,报送请示的案件数逐年上升,已经超过最高法院两个通知中规定的范围。案件请示制度既是违法的,又具有现实危害性,应当予以废止。[92]有学者也有类似观点。[93]在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慧芳甚至提出“取消法院内部案件请示”的议案。[94] 面对批评,最高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第12条明确提出,要“改革下级人民法院就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做法”。国家法官学院主办的刊物《法律适用》曾特别策划专题讨论“案件请示的诉讼化”问题。浙江金华法官调研发现,尽管法官们拥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三项承诺”中关于限制请示、最终取消案件请示的政策,但对于当下的案件请示基本上都持保留和支持态度。案件请示在当下仍有存在的基础。[95]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对内部请示制度的形成和做法进行了分析,根据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报送刑事请示案件的范围和应注意事项的通知》,报送请示案件只能是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明的案件,且内部请示需要遵循严格的程序,但实践中存在很多以“沟通”“讨论”“交换意见”为名的非正式的案件请示。 对正式的案件请示和非正式的案件请示都应当进行改造。[96]湖北省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则主张将疑难案件移送上级法院管辖。[97] 尽管有各种规定来规范案件请示制度[98],改革案件请示的主张时有出现,反对案件请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案件请示制度一直以正式或不正式的方式运行着。实践中,下级法院遇到疑难问题往往会请示上级法院。其具体做法分为三种,一种是较为随意的沟通,在法院内部院庭长讨论案件时,如果院庭长遇到拿不准的小问题,往往会通过电话的方式与上级法院沟通,在得到明确答复后再决定如何处理;另一种则是较为正式的讨论,在遇到较为复杂的案件时,为了避免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对基层法院的考核造成不利影响,院庭长会联系上级法院的对口部门,然后与承办法官一起去上级法院对口部门汇报讨论案件;最后是正式的请示与答复,即一审法院以书面方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以书面方式答复。相对来说,前两种非正式的请示较多,最后一种正式的请示实践中并不多。一般来说,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下级法院为了在考核中获得较好成绩;二是下级法院将矛盾上交,或者借上级法院抵御各种干涉。[99]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而言,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有可能是想将矛盾上交,也有可能是试探上级法院的底线,还有可能是通过向上级法院“做工作”,希望上级法院支持下级法院作出的决定。 接下来的问题是,上级法院为何会接受下级法院的请示?又为何会支持下级法院作出的决定?就前一问题而言,主要原因有三:(1)上级法院相关人员与下级法院的复杂关系。司法实践中,下级法院与上级法院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另一方面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领导往往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下级法院在年终或者节假日会邀请上级法院的相关人员吃饭、娱乐等,俗称“做工作”,之后,原先的工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因此,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案件并不需要遵照有关案件类型的规定。(2)统一辖区内的法律适用。上级法院不仅要处理下级法院上诉来的个别案件,还要在辖区内统一法律适用,如一定时期司法政策的贯彻、领导讲话精神的领会等,通过讨论案件,一方面可以解决具体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传达最新政策精神(至少是领导讲话精神),从而实现在辖区内统一司法的目的。(3)上级法院的默许。事实上,在上级法院内部,对于这种“非正式”的案件请示制度基本持认可的态度,甚至个别领导还鼓励这种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沟通。有的上级法院的部门领导对下级法院请示的案件一般要求下级法院写出“案件讨论报告”,同时收集相关材料并做好讨论记录,在年底总结时这些将是部门工作成绩的一部分。[100] 关于后一问题,主要原因也有三个:(1)上下级法院法官之间的密切关系,意味着上级法院不能随意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101],否则还有谁愿意与你“交朋友”,况且上级法院的相关人员偶尔也需要通过下级法院对个别案件“打招呼”;(2)证明标准的弹性以及上级法院原则上尊重下级法院判决的传统,意味着上级法院没有充足的理由,一般不会改变下级法院作出的判决;(3)上级法院可能也会面临各种压力,如被害方、社会舆论以及党和政府的压力。 综上,由于证明标准所具有的弹性,法官可以通过滥用自由裁量权不排除非法证据,由于案件请示制度的存在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特关系,下级法院作出的决定基本上不会有改判的危险。各种原因的结合,最终使得法官能够不排除非法证据。 七、结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在这一大的背景下,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牵头制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现有的非证据排除规则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均予以相当大的完善。毫无疑问,《规定》如能及时出台,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这种法官不排除非法证据的状况。然而,我们在此仍需要研究与反思法官为什么不排除非法证据,否则,《规定》出台后,仍可能面临法官因各种原因而不排除非法证据的困境。 根据上文的分析,法官不排除非法证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僵化的司法思维(能动性不足,对司法解释的迫切需求)、有诉必判和追诉优先的审判理念(定罪是目的,其他是手段)、一体化的司法体制(侦查本位、法院不独立不中立)以及行政化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庭审非中心,法官是“代理”,裁判结论既不完全形成于法庭上,也不完全以心证和确信为依据)等,可能对法官不排除非法证据都有贡献。对此,应根据不同的原因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加强法官的业务知识培训和司法理念培养;(2)在公检法机关之间,要确立“审判中心主义”[1],公安检察机关关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判断在服从于法院的最终裁判,确保法院的裁判对于公安检察机关具有权威性;(3)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上级法院尊重下级法院的裁判,注重发挥审级制度的功效;(4)在同一法院内部,要逐步落实“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原则,保证审判法官和合议庭能够独立裁判、中立裁判;(5)既要实行案件裁判终身负责制,也要健全审判人员依法履职保护机制,保障审判人员依法行使审判权不受追究。 【作者简介】 王彪,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注释】 [1]《中政委规定》第1条: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外,应当在规定的办案场所进行;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不得以起赃、辨认等为由将犯罪嫌疑人提出看守所外进行讯问。 [2]《高法意见》第8条: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3]参见孙长永、王彪:《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75—77页。 [4]根据海口、西安、廊坊、宁波等地与会法官、检察官代表在某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总结,实践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法院“不敢排、不想排、不能排、不会排、排不动”,检察院“有监督之名、无监督之实,事前无法预防非法取证,事后无法证明取证合法”。参见陈卫东、柴煜峰:《“两个证据规定”实施状况的真实调研》,载《法制日报》2012年3月10日,第10版。 [5]申请启动率是指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数与因申请而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案件数之比。笔者有幸全程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牵头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新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制定,以上数据系笔者在参与调研中获取,为遵循学术规范,将相关地名隐去。下文的实证材料如果没有特别指明出处,均为笔者调研所得。 [6]参见王超:《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难以激活的原因与对策》,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6期,第145—147页。 [7]尚权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调研报告中有类似观点,即在法院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际状况是:第一,关于启动的条件,法院不仅要求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证据材料,还要求所提的线索或证据材料具有一定的证明力,否则不予启动。第二,对控方的证明责任持纵容态度。第三,人民法院对辩方的申请置之不理。第四,法院虽启动了排除程序,但对争议对象是否属于非法证据,不作评价。参见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编:《新刑诉法实施状况调研报告(2013年度)》,第17页。 [8]该学者以樊奇杭案为例,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辩方已履行提供侦查人员涉嫌非法取证的证据后,仍然没有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做法,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的贯彻实施,起到了一个非常坏的示范作用。参见郑飞、樊传明:《论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未来——以内部结构与运行环境为切人点》,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96页。 [9]参见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07页。 [10]参见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第52页。 [11]参见万毅:《解读“非法证据”——兼评“两个〈证据规定〉”》,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2期,第30页。 [12]关于基层法院法官的工作量和压力,参见孙长永、王彪:《刑事诉讼中的“审辩交易”现象研究》,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1期,第130页。 [13]参见戴长林:《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运行效果简析》,载《法制日报》2014年11月12日,第5版。 [14]参见杨宇冠:《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问题研究》,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8期,第107页。 [15]参见吴宏耀:《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第123页。 [16]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页。 [17]参见龙宗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痛苦规则”及相关问题》,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5期,第18—22页。 [18]参见程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范分析》,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第186页。 [19]参见黎宏伟:《非法证据排除与侦查谋略——以“威胁、引诱、欺骗”获取供述为例》,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4期,第81—82页。 [20]参见王彪:《审前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研究》,载《证据科学》2013年第5期,第594页。 [21]参见谢小剑:《重复供述的排除规则研究》,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1期,第113页;闫召华:《重复供述排除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2期,第128页;林国强:《论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32页。 [22]参见万毅:《论“反复自白”的效力》,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43页。 [23]参见田文昌、邹佳铭:《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若干问题》,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7期,第68页。 [24]《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官也应当进行调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0条:经法庭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可以当庭宣读、质证:(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已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三)公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 [25]参见张军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页。 [26]关于“小河案”非法证据排除的顺序之辩,参见唐宁:《政协委员被控涉黑三年三审——贵州黎庆洪案重审疑云》,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2年1月16日,第A03版。 [2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同志认为,法庭审判的具体顺序,应当由上述审判组织根据充分发挥庭审作用的需要来确定。正是基于上述考虑,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法庭调查的顺序由法庭根据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参见李寿伟:《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2期,第62页。 [28]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再讨论》,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69—170页。 [29]参见戴长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9期,第26—28页。 [30]参见顾永忠:《我国司法体制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2期,第105页。 [31]参见胡红军、王彪:《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疑难问题》,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8期,第64页。 [32]参见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第93页。 [33]参见王彪:《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威慑效果实证分析》,载《河北法学》2015年第1期,第116页。 [34]有学者认为中立原则是刑事审判程序公正的标准之一,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9页。 [35]邓楚开:《面对“追诉型法官”要据理力争》,载法律博客http.//dengchukai.fyfz.cn/b/833350,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6日。 [36]参见李昌盛:《刑事庭审的中国模式:教化型庭审》,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1期,第131—133页。 [37]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38]王超:《排除非法证据的乌托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85页。 [39]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法官认为,作为对诉讼制度的一种理论阐述,“庭审中心主义”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其中就包括“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参见蒋惠岭:《重提“庭审中心主义”》,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4月18日,第5版。 [40]参见陈柏峰:《从乡村社会变迁反观熟人社会的性质》,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第101页。 [4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42]参见王彪:《刑事诉讼中的“逮捕中心主义”现象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2期,第78页。 [43]参见陈瑞华:《司法审查的乌托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实施的一种成因解释》,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8页。 [44]陈光中、郭志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若千问题研究——以实证调查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9期,第7-8页。 [45]参见李昌盛:《违法侦查行为的程序性制裁效果研究——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3期,第119页。 [46]陈卫东、程雷、孙皓、陈岩:《“两个证据规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侧重于三项规定的研究》,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1期,第78页。 [47]一审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理由如下:公诉机关虽然出示、宣读了章国锡的有罪供述笔录、播放了部分审讯录像片段、提交了没有违法审讯的情况说明等,但没有针对章国锡及其辩护人提供的章国锡在侦查机关审讯时受伤这一线索提出相应的反驳证据,无法合理解释章国锡伤势的形成过程,其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获取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故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关于章国锡案一、二审审理情况,参见苏家成、俞露烟:《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12年第18期,第61—66页。 [48]参见孙长永、王彪:《刑事诉讼中的“审辩交易”现象研究》,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1期,第132页。 [49]参见李海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情况之实证研究——以东南地区某法院为例》,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1期,第105页。 [50]参见万毅:《“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法理研判》,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6期,第661页;王彪:《审前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研究》,载《证据科学》2013年第5期,第601页。 [51]具体案情,参见管友军、郑晓红、陈克娥:《褚明剑受贿案——法院如何审查受贿案件辩方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9集),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3—94页。 [52]参见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第1125页。 [53]参见陈瑞华:《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1页。 [54]参见刘静坤:《避免虚假印证防范冤错案件》,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3月5日,第6版。 [55]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证据法实施情况调研”课题组:《刑事证据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以西部四省部分公安司法机关为考察对象》,载潘金贵主编:《证据法学论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56]关于程序安定理念与刑事既判力理论,参见施鹏鹏:《刑事既判力理论及其中国化》,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0—170页。 [57]关于既判力理论与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联系与区别,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载《政法论坛》20年第5期,第115—132页。 [58]参见黄士元:《刑事再审制度的价值与构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59]参见龙宗智:《审判管理:功效、局限及界限把握》,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21—39页。 [60]艾佳慧:《中国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研究——“同构性”和“双轨制”的逻辑及其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第75页 [61]朱桐辉:《案外因素与案内裁量:疑罪难从无之谜》,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5期,第30页。 [62]参见汪庆华:《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63]参见王彪:《论基层法院疑罪处理的双重视角与内在逻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4页。 [64]有学者遴选了1986年以来的20个典型冤案,其中就有9起案件地方党委、政法委甚至同级政府部门进行了干预,其中,4起以“三长会”的形式进行协调,5起以其他方式进行协调。参见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载《中囯法学》2007年第3期,第57页。有学者则认为,在政法委协调办案的潜规则下,政法委对于冤案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一锤定音。参见严励:《地方政法委“冤案协调会”的潜规则应该予以废除》,载《法学》2010年第6期,第40页。 [65]参见龙宗智、袁坚:《深化改革背景下对司法行政化的遏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32页。 [66]翁子明:《司法判决的生产方式——当代中国法官的制度激励与行为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页。 [67]陈兴良主编:《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150页。 [68]参见王彪:《基层法院院庭长讨论案件机制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0期,第68—69页。 [69]参见李红辉:《反思与出路:改革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载《求索》2012年第6期,第228页。 [70]第一篇讨论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的论文发表于1980年初,该文作者为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该文认为,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没有法律依据,有诸多弊端。参见刘春茂:《对法院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的探讨》,载《法学杂志》1980年第2期,第34—36页。该文发表后,许多其他法院的法官纷纷撰文支持该作者的观点。参见冯建:《法院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违反集体领导原则》,载《法学杂志》1981年第1期,第26—27页;向诚权:《关键在于提高审判人员的质量》,载《法学杂志》1981年第1期,第27—28页;凌云志:《保证合议庭依法行使职权》,载《法学杂志》1981年第1期,第28页;罗德银:《院长批案不可续》,载《法学杂志》1981年第2期,第37—38页。 [71]有趣的是,上述支持刘春茂的作者均为其他地方法院的法官,而北京高院和北京二中院的法官则均认为院庭长讨论案件没有违法,应当予以坚持。参见文实:《人民法院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并不违法》,载《法学杂志》1981年第2期,第39—40页;孙常立:《法院院、庭长审批案件是完全合法的》,载《法学杂志》1981年第3期,第44—45页。 [72]该法官认为,要杜绝“先批后审”,审理后,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提出判决意见,仍应报庭长或院长审查签发,但庭长、院长要尊重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的意见,需要改变判决的,需要与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商量,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不同意改变的,院长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参见贺伦麒:《对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的看法和意见》,载《法学杂志》1981年第3期,第。47页。 [73]参见刘春茂:《对法院院长、庭长个人审批案件问题的探讨》,载《人民司法》1980年第12期,第29—30页。 [74]参见孙常立:《法脘院、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不能取消》,载《人民司法》1981年第4期,第12—13页。 [75]参见人民司法社论:《关于院、庭长审批案件问题的探讨》,载《人民司法》1981年第6期,第2—6页。 [76]徐教授认为,我国的审判独立有其特殊性,院长审批案件与审判独立不矛盾,但要制定必要的领导审核案件的办法,改进目前实行的院长审批案件的做法。参见徐益初:《法院院长审批案件与审判独立》,载《人民司法》1981年第6期,第6-8页。 [77]具体内容,参见张丕穆:《人民法院案件审批制度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8—10页。 [78]参见王永臣:《人民法院案件审批制度需改革》,载《人民司法》1988年第11期,第9—11页。 [79]参见张民:《按厢司法规律改革案件审批制度》,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10期,第26—27页。 [80]参见周晓笛:《还审判权于合议庭——废除案件审批制度的思考》,载《法律适用》1999年第9期,第35页。 [81]参见李秀霞:《三权分离:完善司法权运行机制的途径》,载《法学》2014年第4期,第51-52页。 [82]参见王彪:《一审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程序问题研究》,载《人民司法》2012年第19期,第48—51页。 [83]系统的论述,参见王彪:《犯罪主观要件证明问题研究——以证明困难的产生与克服为视角》,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12页。 [84]参见秦宗文:《自由心证研究——以刑事诉讼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85]参见龙宗智:《推定的界限及适用》,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115页。 [86]黄维智:《刑事证明责任研究——穿梭于实体与程序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87]参见〔美〕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88]参见侯猛:《政法传统中的民主集中制》,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4页。 [89]参见万毅:《历史与现实交困中的案件请示制度》,载《法学》2005年第2期,第9页。 [90]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91]参见张庆国:《关于法院案件请示的若干思考》,载《云南法学》1998年第4期,第76—79页。 [92]参见李华:《案件报送请示制度剖析》,载《法学》1997年第2期,第40—41页。 [93]参见徐纯科:《评刑事诉讼中的“疑难案件请示”》,载《中外法学》1989年第3期,第15_18页;谭世贵:《案件请示制度:是否还有出路?》,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9期,第58—59页。 [94]参见赵萤:《下级法院上访显露弊端取消案件请示呼声再起》,载《南方周末》2009年5月21日。转引自庞景玉、何志:《浅议案件请示的改革路径》,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15期,第104页。 [95]参见徐建新、毛建青、吴翠丹:《案件请示制度的问题与实践分析》,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8期,第8—11页。 [96]参见蒋惠岭:《论案件请示之诉讼化改造》,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8期,第2—5页。 [97]参见霍焰:《疑难案件移送上级法院管辖中的问题——以案件请示制度之诉讼化改造为背景》,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8期,第5—7页。 [98]具体的梳理,参见佚名:《案件请示做法的由来》,载《法制资讯》2009年第5期,第56—57页。 [99]参见陈瑞华:《为中国“案件请示”把脉》,载《法制资讯》2009年第5期,第54-57页;毋爱斌、王聪:《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审级保障——以案件请示制度为切入点》,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2期,第84—85页。 [100]参见王彪:《法院内部控制刑事裁判权的方法与反思》,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2期,第73页。 [101]有学者认为法院内部的考评制度和案件请示制度导致上诉审理流于形式,参见朱立恒:《刑事审级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对绩效考评与案件请示做法的批评,参见廖明:《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评析——以刑事审判业务为视角》,载张军主编:《刑事法律文件解读》2012年第1辑(总第79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 [1]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含义与理论依据,参见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第93-94页。 |